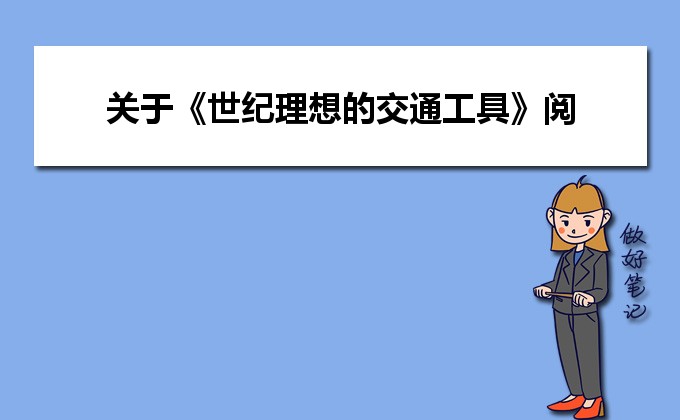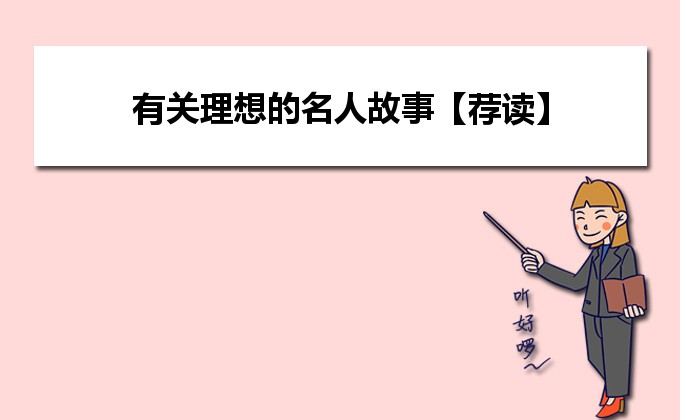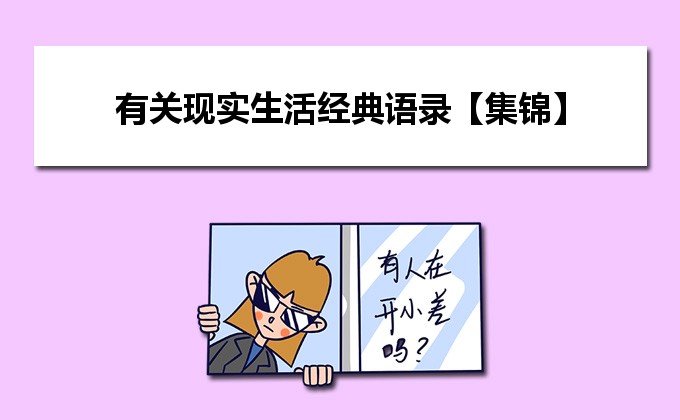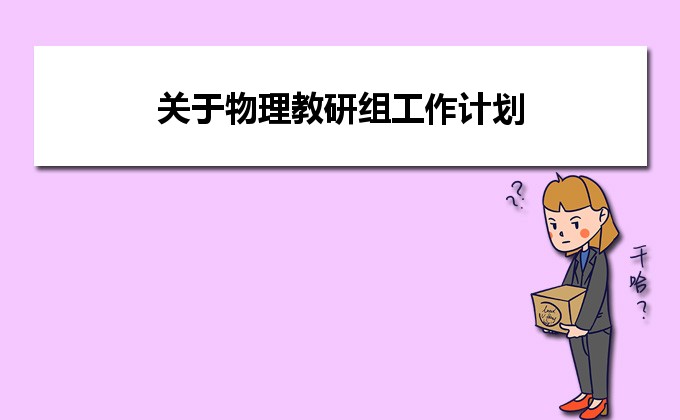今天,我想谈谈大学,谈谈理想。
201x年11月21日的下午,广西师大王城大礼堂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一场思想与智慧的碰撞拉开了序幕。这是最后一场沙龙压轴戏,为的是庆祝广西师大出版社的25岁生日。两位学者,著名节目主持人梁文道和画家陈丹青的到场让现场一度火爆。主题是《谈谈大学 聊聊理想》。
梁文道先生开头场,负责讲“大学”部分。从中国式的教育制度讲起,再到国外的教育。他提到一个特别值得思考也是一个老话长谈的问题:中国式教育,即家长包办教育,政府官办教育,学校精英教育等。梁先生说,中国的孩子从小被灌输所谓的主流思想,被灌输父辈的官本位、“知识有用无用论”等思想,孩子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生活教给他们的只是条条框框的东西,全是别人说怎么样就怎么做,没有自己的话语。学生不敢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一旦说出来,心想,“哦,爸妈可能不同意,学校社会可能不会接受吧,他们不理解也不会答应,那还是算了吧。”爸妈不懂,跟他们讲简直是“对牛弹琴”、“鸡对鸭讲”。其实他们还是懂一点的,
因为我们触动了他们的底线。闹僵的结果只有发飙式的“反抗”了,不是出走就是关起门来自我封闭。一个发自内心的想法刚刚萌芽,原本可以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是由于社会、家庭的束缚和阻碍,它还未成长,就被死死地扼杀在摇篮里。这或许就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吧。
再谈国外教育,梁先生从王城校区说起,他说很少看过这么有富有历史底蕴又不乏美感的校区,当然也很少看到哪个校区要收费、门票还不低的。这是一个切入点。国外的教育很讲究开放性,我们的大学,一方面是“学”,即可看作一个综合的实验。所以在实验过程过,出现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因素不仅不应该以打击异类的心态看待,而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包容心态理解并加以引导。另一方面是“教”,大学是培养人才,就是出成果了。因此大学的目的就不仅仅是盈利或闭门造车了,而应该是带着“普世”的精神,让大学变成一个真正为全国、全人类、全世界服务的教育基地。
从梁先生话中,我读到了中国教育制度“官本位、重功用”的根深蒂固,也读出了中国的特有教育。
提到“理想”,让我感到震惊的是画家陈丹青先生。他提到自己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竟然是我们老家宁都。他说,老百姓对这些下乡的青年还是一知半解,以为“知识分子的下乡就是和老百姓抢饭碗”。知青的处境可见一斑。我们的祖辈父辈那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可如今,有些老区的人民依然没摆脱温饱。
陈先生在文革下乡时期可以说没有理想,只有一些欲望。他承认,自己小时候的理想是当画家。一个从乡下一直跟随他到美国纽约,就连做梦都想起的最大“理想”竟然是希望调到当年插队的隔壁乡镇-??对坊乡!原因是这个乡“靠马路,人多”。这个真实而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理想与其说是理想,不如说是欲望。以致现在的他都分不清什么是理想和欲望。
其实他对理想是模糊的,但是对理想的追求却十分清晰。而这种理想在他看来不是从小就能实现的,欲望和理想的分界岭是大学,78年恢复高考让他重获希望。读大学后才知道,原来自己当时的理想只不过是一些欲望的叠加,最后才演变成所谓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后来又慢慢变成了欲望,此时的欲望已经不是理想了。因为理想实现了,可接着欲望又来了。当欲望变成理想后,欲望又开始了。有些时候,我们不也一直徘徊在欲望和理想中吗?从他的讲述中,我读出了那个为理想坚持不渝的人格魅力,还有他内心的伤痛。
对于大学,众说纷纭。诚如我们读《丑陋的中国人》一样,“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就像孙观汉先生《环境与地气》里讲的一样,用种田人的言语来说,问题不在“种子”,而在“地气”,地气就是环境,包括人性的习俗。一谈中国大学,说好是“牛”,说差的一个字“烂”。大学不是说说就会变成大学,但是不说就永远只是中学或小学水平。我们的学生缺少的是和父母的沟通,我们的大学就像一个人,外表很彪悍,但是心灵却很脆弱。相比之下,国外的大学却是不管外表平凡或高贵,内心要强大。因此,我们的大学需要的不是“上传下达”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是和家长、政府、社会沟通后的抉择。我们的悲观或是乐观,亦是达观;我们的大学感性或是理性,皆是人性。
对于理想,没有绝对定义。在农民眼里,种粮丰收是他们的理想,在知识分子眼里,传道授业是他们的理想。可是我们很多时候理想偏离了轨道或者不在轨道上,也只是把理想当欲望,而且也能想出很多追求欲望的方法,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想,也能说出许多实现理想的途径,但是能真正去做并坚持下来的少之又少。
我的大学曾经就是我的理想,现在我的理想实现了,可我的欲望也来了。我的理想慢慢地疏远了我。在理想的国度里,我偶尔也会迷失方向。
所以,我也担心,某一天我将成为柏杨笔下丑陋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