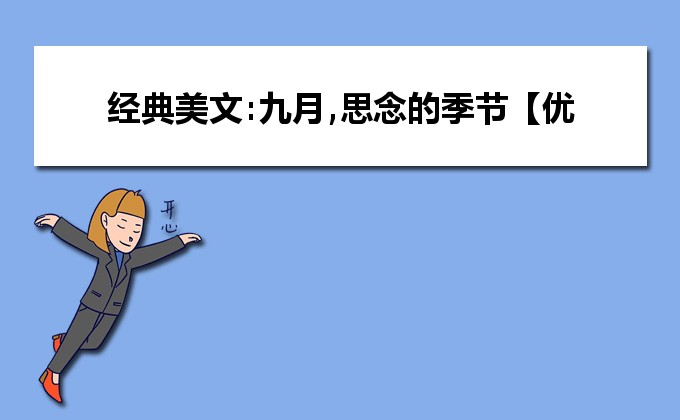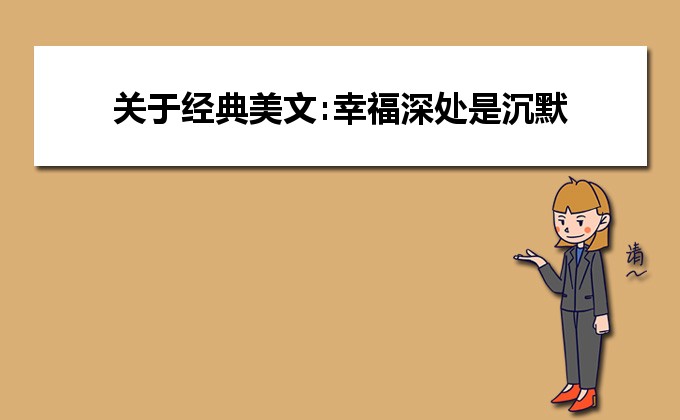?包草学名叫什么,我至今尚不得而知。四川人把咳嗽气喘的人叫作?包,能治这种病的草,自然就被叫作了?包草。;?包草不象别的草儿般随地皆是。在我的家乡,有?包草的地方实在不太多,?包草便因了它的少,而显得比别的草贵重了一些。只是,?包草却又并非单珠独立,凡有?包草的地方,几乎都是密匝匝一小片。它们匍匐在草地上,圆圆的,如拇指般大小的叶子,象一把把撑开的绿色小油伞,把伞下的秘密盖了个严严实实,任我们睁大双眼也看不透。
;我说过,小时候,我是个“病秧子”。我能不能长大?这个问题,在我八岁以前,父母的心中,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面对没有答案的问题,很少有人的心能安定下来。我父母的心,因此悬悬的吊了好多年。当然,这是我若干年后才感悟到的。
我又病了。发烧,咳嗽,喉咙里嚯嚯地拉着风箱,耷拉着脑袋,双眼无神,上气接不上下气。母亲很着急,放下队里挣工分的活,心急火燎要背我去医院。可进医院那道高高的门槛,得要一种叫“钱”的东西。母亲口袋里没有一分钱,只好诚惶诚恐地向父亲要。父亲的脸黑得象马上就要下雨的天,吼声差点把茅草盖的屋顶掀翻:我又没造钱。束手无策的母亲用艰难挤出来的笑与感激之词,从邻居那儿借到了五角钱。
母亲背上轻轻的我,揣着沉沉的五角钱,直奔医院。已经对我非常熟悉的老医生给我仔细检查后,对母亲说:是肺炎,要输液,要住院。母亲手里紧紧捏着那五角钱,仿佛一松手,我的命就会随着那张钱一并随风而逝。母亲喏喏地说:我只有五角钱。好心的老医生叹一口气:我先帮你掂上五元吧。
我输上液,母亲急急来到街上,找了个熟人带信,告诉父亲我的情况。母亲总是害怕面对父亲,好象我的病,是她造成的。下午回到家,猪圈里唯一的那头架子猪不见了,听说,父亲为了能尽快地把它卖出去,少卖了五块钱。这让母亲很心疼。母亲用卖猪的钱,天天背我去医院。十天后,我的病好了,而卖的那头猪,却连一只猪蹄的钱都没留下。
父母悬着的心,落回原处还没躺舒服,我又着凉了。我象一只怕冷的小猫咪,蜷缩在床上。不时的咳嗽声伴着嚯嚯的喘息声,穿透房间的每个角落。那声音,又将父母的心高高悬起。多年后,我依然能想象:当年,我的每一声咳嗽声,会象一把高高抡起的?锤,重重地击在父母悬吊着的心上;而喘息声,则是一把巨大的剧齿,从早到晚,恶毒地撕裂着父母已被?锤击伤的心。父亲母亲的心,被囚禁在这些声音里,无处可逃。
父亲黑着脸,喘着粗气,站在房门口,远远的看我。半晌,父亲说:要死。干脆死了算了。父亲扛着锄头出门了。锄头上沾满的忧伤,沉重地压在父亲的肩上。直至今日,我时常想到父亲这句话,内心里却一点也没有怨恨的感觉,有的,只是对父亲的内疚与心疼。当年,父亲在说这句话时,有着多少无奈,心痛与绝望,我能想象。母亲对“死”这个字深恶痛绝,尽管她有着比父亲更多的无奈,心痛,绝望。母亲站在我的床边,摸摸我的额头。还好,不发烧。母亲试探的说:出去和她们玩会儿吧,兴许,玩的高兴了,便忘记咳了。
我也说过,我的家,曾是周围孩子们的“革命根据地”。那时,有小孩们正在根据地里嘻戏玩耍,飞进屋来的欢声笑语里,满是健康的味道。这味道,让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多么希望这些明快的笑声里,也有着自己女儿的一份。
我爬起来,无精打采地走到屋外。一道关切的目光,如影随形,尾随着我来到屋外。这目光提心吊胆,充满忧郁。我靠在门边,屋外明亮的阳光,让我不得不眯缝了双眼。三儿与几个女孩子在屋檐下“抓子儿”,几个男孩子在地上滚滚爬爬地打着弹珠。三儿看到我,问:你来不来?我摇摇头,走过去,为了让自己舒服些,我在她的旁边蹲下来,看。直到现在,我都习惯于“蹲”这个姿势。但当时,这个姿势却并未让我舒服太久,只一会儿,我便又想躺回床上。于是,那道忧郁的目光又随着我回到屋内,看着我躺在床上。
母亲在床边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出去了。我在叹息声中,恍恍惚惚地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听见母亲在叫:狗儿,来,快把这吃了。母亲是在叫我。在家里,母亲叫我狗儿。母亲说,狗有七条命,叫狗儿的孩子容易养活。母亲坚信,我最终能被养活,长大,跟她一直坚持叫我狗儿有莫大的关系。我睁开眼,看到母亲端着的碗里有半碗黄白绿相间的食物。我闻到了鸡蛋的味道,很香。吃了,就不会再咳了。母亲又说:这是专治?包的药。药?我拿着筷子的手,有些迟疑,药字在我心中,就是苦涩难咽的代名词。一点都不苦,你尝尝。母亲说。在母亲期待的目光下,我把碗里的东西挑了一点儿在嘴里,真的,一点也不苦,甚至,因为有鸡蛋的香味,我觉得很好吃。如果所有的药都是这样的味道,而我家里又不缺钱的话,我想,我是很愿意自己生病然后吃下这样味道的药的。
吃完了母亲煎的?包药,又睡了一觉,醒来后,咳嗽居然真的减轻了许多。第二日,母亲再去为我摘?包药时,我便也跟了去。一小片葱郁的?包草,紧紧挨挨地挤在一块凹地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些撑着绿伞的小身子,它们,能治我的病。对此,我感到无比好奇。以后,我又吃过多少次母亲给我用蛋煎成的?包药,我已记不清了。十岁之后,我的病竟然慢慢痊愈,到如今,也是从未复发过。这其中,不知有没有?包草的功劳。我相信应该是是有的,母亲也相信。
前段时日,偶然路过那片摘过?包草的地方,看见它依然静静地长在原处,当年母亲带我摘?包草的情景,那么清晰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包草一如当年那般翠绿,葱郁。我的母亲,早已华发满头,步履蹒跚,苍老羸弱的身体,让人不忍细看。那个当年在深夜里背负着我都能疾走如飞的母亲,如今,连自身行动都得靠了第三条腿的帮助。看着眼前的?包草,我猛然感到天地自然的悠然长久与人间光阴的易逝。?包草年复一年枯荣在亘古不变不断轮回着的四季里,今秋虽枯萎,明年会再度葱荣。而我的母亲,却是再也不能回复当年的健康,年轻。我在渐渐模糊的?包草里,看到了正在枯萎下去的母亲……
我蹲下身,拨弄着一把把小绿伞,从拂开的缝隙中,忽然看到了遮盖在伞下的秘密。原来,那里面藏着的,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