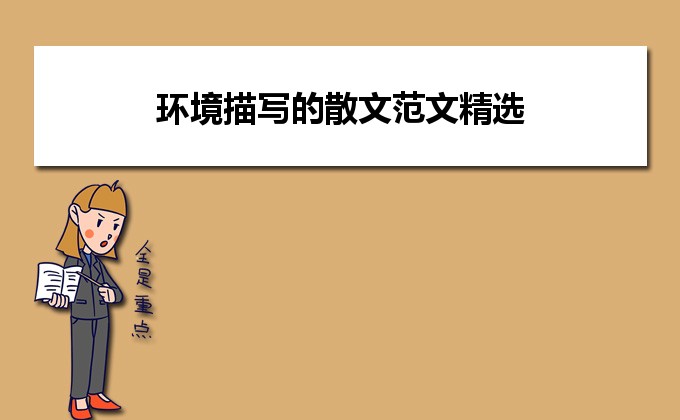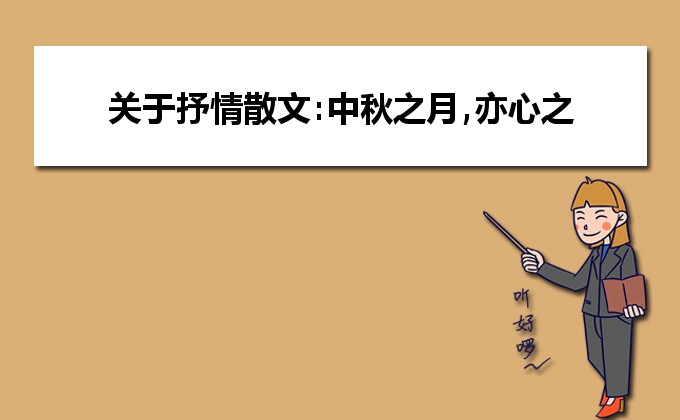在仲夏的某个阴雨天的傍晚,我们带着一些憧憬,欣喜和淡淡的迷茫,第一次来到了我魂牵梦绕了三十年的西湖。从我孩童时起,我就读过许多关于西湖的名篇,因此她在我心中也承载了我太多的期翼,太多的梦想。历史的沉淀是如此的厚重,以至于我许多次从她身边路过也不肯贸然前来。无数次的经验告诉我,梦想中的场景总是比现实中的要充沛而又空灵得多。淅淅沥沥的雨中,西湖就这样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岸柳回廊迎着风雨悄然相立,并没有因为我这个远道而来的游人表露出些许的惊喜。迷蒙的远山在粼粼的波面那边,蹲守着千百年来的某个姿势,寂然无语。而那一抹长长的绿色丝带,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白堤。漫步在岸边,看着那密集的游船,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被西湖感动:躁动的尘世有太多的尘土掩遮了我的心灵,我已经变得如此麻木和迟钝。
混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慢慢地一些若有若无的思绪在我脑海里时隐时现。也是在这样的雨天吗,白居易坐在哪棵树下轻声低吟那首穿越千年的诗篇?又是什么让苏东波流连忘返,佳句天成?吴歌晚唱,又是在哪一个雨天,许仙和他的娘子致命邂逅?浩淼的西湖水,真的都是白蛇的眼泪?或许千百年前我已经来过此地,
那困顿的波澜中也许还残留着我当年遗失的一滴泪。可是,我究竟是在哪一个故事里失落的呢?漫长的岁月留下如此动人心魄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却不知身已何处。西湖的水一次一次洗刷着湖岸,仿佛在一次一次擦尽岁月的尘埃,不让人们把那悠悠的往事遗忘。然而如织的游人又有几许是来找寻那些消失了的悲欢离合,又有几许人肯静静谛听湖水深情的诉说与呢喃?他们频繁地举起相机,想要把自己挤进西湖的山水中,却浑然不知,离开了人的灵性,得到的只是一些堆砌的色彩而已。没有心灵的互动,山不过是高一点或矮一点的山,水不过是宽一点窄一点的水,岸也不过是直一点弯一点的岸而已。
天渐渐昏暗下来。一对恋人相拥在湖水边。湖水把他们斑驳的身影揉搓着,展开着,仿佛要从哪些褶隙里找寻一些元素。湖水轻声细语着,宛如在低问来人:若干年后,您们还会同来此地,回忆哪些温馨的往事么?重拾哪些甜蜜的时光么?太多的旧事沉沦在湖水底下:她多少次看见海誓山盟的城墙在世俗的狂风暴雨中轰然坍塌,又多少次看见时间的利刃把谎言的羽毛一片片剥落。只有少数人硕果仅存,可是其中又有多少能再次同温旧梦?岸边的垂柳在凉爽的晚风中轻轻摇动长长的披发,低头不语。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西湖边,乘坐渡船去到湖中的三潭映月。阳光映照在湖面上,潋滟的湖水宛如一幅巨幅的墨玉色绸缎在船底下飘曳。习习凉风扫走船头夏天的郁热,西湖美景扑面而来。熙熙攘攘的游人指指点点,儿童欢快的奔跑,和导游那喧闹的扩音器,使人无法静静感悟什么。过多的游船来来往往把西湖切割成一段一段。假如东坡再世,再也无法吟诵出扣人心弦的诗歌。而渐渐在眼前放大的是法海的丰碑,那就是雷峰塔。其实许仙和白蛇并没有干他什么事,但是法海有一沓沓规矩和典籍,他的一生就是以此为荣为生,假如逾越它们也能活的如此滋润,那他岂不是白活人世了。如是在痴情的白蛇和正义的恶棍法海之间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冲突。终于,白蛇失去了她的许仙。千百年来,她静静躺在塔底,静静守望着她的爱情的家园。如今,法海的塔早就垮塌了,但她依然在那里久久守望。没有了许仙,她的灵魂无处栖息,她只剩下这个家园了。可是,在这个日益追求肤浅的色彩和感官享受的世界里,有谁还能象她那样无怨无悔的守望?西湖的水真是她孤独的眼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