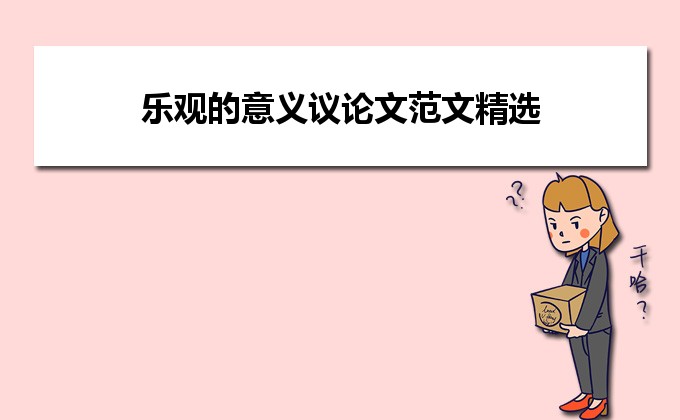近年来,国学、国学阅读和国学教育,几乎成为人们谈论思想文化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眼下,无论手机、电脑还是电视、广播、书报刊等,有关国学的内容和专栏比比皆是。社会上各种国学培训班也是纷纷开办,一时间新一轮“国学热”高潮迭起。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正确看待国学热议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篇一:正确看待国学热议论文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篇二:正确看待国学热议论文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是经济带动了文化?或曰是二者互动?然而,所谓"互动",总有个谁先动、谁后动的问题,笔者是绝不同意那种把东亚经济崛起归因于文化动因的观点的。实则,是先有经济的崛起,后有文化的跟进沾光,再有文化对经济的回光反照。不然的话,中国文化在那里至少已经"动"了三千年了,何以今日才使得洋人刮目相看?总之,作为文化,归根到底,还是随着经济的繁荣而繁荣。
“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
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行。孔子思想就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认为对包括孔子在内的人类知识财富学习得越少越好的人,按列宁的话说,是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匡亚明认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也离不开和传统文化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孔子思想的精华)并非格格不入,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二者虽然相隔两千余年,但历史连续性规律使它们仍带有相通之处。孔子在封建社会提出了大同思想,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共产主义与大同思想都强调“天下为公”。马克思讲国际主义,孔子也强调他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国际”主义,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尽管表达的方式不同,内容也不相同,但基本精神有相通之处。由此可见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含有真理性或可贵的智慧萌芽,是有生命力的,是可以而且必须做到使之为当前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
上述论断,便是匡亚明在《求索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表述的基本思想。
匡亚明这种思想使我们想到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的呼声遍于中国大地,而郭沫若却是逆着当时的反孔潮流的。他写道:“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就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了。”“我在这里告白:我们崇拜孔子。说我们犯时代错误的人们,那也由他们吧,我们还是崇拜孔子。”1924年,他甚至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假借孔子与马克思的对话,赫然写道:“我们的出发点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孔子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马克思讲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等,孔子拍手叫道:“你这个理想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我的思想乃至我国的传统思想,根本和你一样,总要先把产业提高起来,然后才来均分。”马克思感叹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对于孔子,杜国庠、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等都曾明确表示过反对,但郭沫若、匡亚明的态度却表明:尊孔与反孔,并不是区分一个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反孔,也可以尊孔。
公允地讲,大陆的儒学人士,一般都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主流的研究者都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和言论,在大陆也不容否定,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敢太张扬而已。例如,有人这样写道: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如此激烈的言论,正反映了许多儒学人士的"灵魂"。
应该承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两种自成体系的思想形态,其产生的时代、理论指向均不相同。笼统地一般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显然不合适。但是,形而上学地将二者截然打成两截,不承认两者有相互融通、交叉的内容,也难服人。
只有形而上学,才在绝对对立的两极思维定式中思维。人文现象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其界限模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具有本质差别。亚理士多德的物理学,如果不是专门研究科学史,现代物理学家不会再去顾及。可是,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现代哲学家却不能不有所了解。有了爱因斯坦,牛顿力学就显得"过时"。可是,有了黑格尔,决不意味着柏拉图的过时。莎士比亚的戏剧精妙之极,但那不意味着咱们的关汉卿就不值一文。曹禺不是关汉卿的代替人,而是关汉卿的对话者。同样,有了马克思,决不意味着黑格尔可以像死狗似地撇在一边。有了毛泽东,也不表示孔老夫子就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了。我们生活在现代世界,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这些物质文明,是古人所没有见到、甚至无法设想的。但是,这并不表明现代人在精神上就一定比古人“进步”。在人文精神领域,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原始”,而古人也可以比现代人更“现代”。真正的“道”,有其穿越时空的功能。古今不同,中西不同,而人心则一。但是,假如就此而断言儒学比马克思主义高明,那就真真是痴人说梦了!
央视隆重推出了“百家讲谈”栏目,一经播出立刻万人称颂,引起“国学”热的风潮。我却冷眼旁观,并坠入深深的迷惘之中。
历年来,人们对文人这一特定的群体,是鄙视的,甚至蔑视他们的存在。人们常用“百无一用是书生”“酸秀才”“迂腐”等词来形容文人,就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时代,在统治着的眼里,文人一样是不堪大任的,真正的文人,也会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
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文人是被遗忘的一个群体。重理轻文的现象普遍存在,英语比国学重要,数、理、化,比写作重要。因为数,理,化学得好,可以找到好的工作,英语学的好,可以到外企当白领,而国学你学的再好,你又能做什么。于是就是喜欢文学的人,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现在国学热了,热的让人难受。一个所谓的“文人”篡改了历史,英雄变成了败类,卖国者成了爱国者,黑的变白的,一觉醒来,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这个“文人”火了,有人视为敢于揭露“真象”的勇士,敢于挑战权威的斗士。还有的“文人”整天说着大逆不道胡话,去迎合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就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还有的人,写几首歪诗,经过文痞一煽风点火也名利双名。更有甚者,有人写一些低级趣味的书,美其名曰“身体写作”,媒体竟然大肆报道,此人也能春风得意。人们不是在忙着做学问而是忙着炒作,就连那些大家也争先恐后找熟人,走后门想在电视上露脸。电视台也适应潮流推波助澜,一股热潮汹涌,席卷神州大地。人们惊叹,国学复苏了。
国学真的复苏了吗?我不清楚。我只记得,我最喜欢散文家的余秋雨,现在写的《千年一叹》,失去了过去文章的深度;我只记得,那些上电视的大家们要么在签名售书,要么在各地讲演;我只记得,文人在绞尽脑汁的想出名;我只记得,文人迷失了自我。有人说,那些人不是真正的文人,可是那些进去也曾经写过好作品的人,现在热衷于名利的大家呢?他们不是也在大行其道吗?只要能吸引人的眼球,管它什么东西,只管发表;只要有银子,狗屁文章照样刊行于世,照样可以名扬天下,照样可以赚大钱。潜心修学的人依然没有人去过问,好作品依然束之高阁。我长叹,国学真热呀。
让国学热降温吧。可怜的文人,刚从人们的蔑视中走出,难道又要踏上一个不归路吗?媒体的造星运动还在进行中,你们成为了这轰轰烈烈运动中的小丑,媒体人,包装公司,在数着钞票消费着你,你成为了玩物,成为了傀儡。你还是个文人吗?“非淡泊无以名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牢记呀。
我衷心的希望国学别热,因为利令智昏。只有给国学一个宁静的空间,国学才能有所发展,才能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