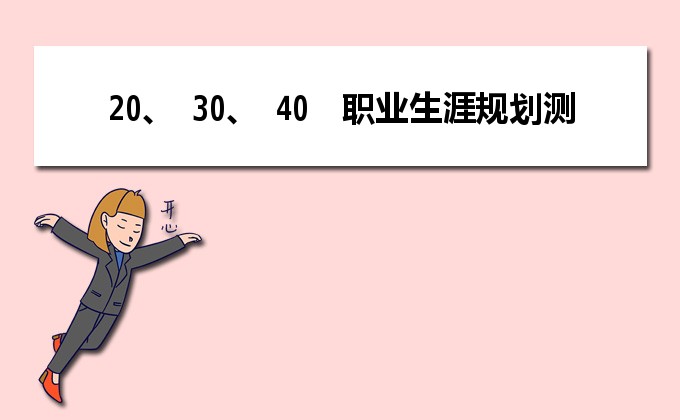一半的时间里,曾小亮两上八宝山。
送走的第一位好友,是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女性频道的主编,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仅37岁。新近送走的是《健康与美容》杂志的主编孟玲和,48岁,开会时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天曾小亮还曾与其彻夜长聊。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曾小亮一个人沿着长安街走了好久。这位酒尚出版人助理、情感职场专栏作家、总是为别人调制“心灵鸡汤”的人,在那一刻,竟然抑制不住心生强烈的幻灭感。
他忽然间觉得,金钱、地位、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生命、健康与爱,这些我们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义,但是长久被忽视的东西,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他们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到迅速富裕;同时也见证了恢复高考、计划生育、打破大锅饭、企业改制、取消福利分房、中国加入WTO等种种既有秩序的被打破。
当秩序被打破时,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代际变迁的印记。
35岁老了?
提前来临的焦虑、无措、迷茫
科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前一阵子刚刚接触了一家叫“豆瓣”的互联网公司。让他这个做了十几人力资源工作的老“猎头”有些意外的是,豆瓣公司员工的平均龄非常小,大概在25岁左右。
大约三前,刘峰和腾讯的HR有次聊天,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腾讯的“特色”之一“很轻”。
近十里,国内一些新晋大公司的出现,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13.42 0.00%]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带动了一个大产业,使很多轻人纪轻轻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而且,互联网等新产业的勃兴,正加速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优胜劣汰,也正拉低着职场人群的平均龄。
互联网领域里“轻化”的公司正日益多起来。比如中国第一家女性团购网站“聚美优品”,三个联合创始人都是80后,一些中层管理者甚至是1989生人,今29岁的CEO陈欧一直有个想法,在自己30岁以前把聚美优品做上市。他甚至坦言,在事业快速发展的这几,他暂时不会因为结婚这类“家事”把自己限制住。
35岁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职场“生死线”,对许多IT人来说,35岁甚至意味着技术生涯的结束。
现在,对越来越多在职场和事业上打拼的80后来说,29岁就已经临近“过期”:青春的有效期29岁截止,一到30岁,就会被打上“Timeout”(过期)的印记。
对于那些最早一批进入外资企业“吃螃蟹”的人来说,现在已近人到中,更是处境尴尬。
一方面由于龄的原因,不少外企白领在公司的发展遭遇瓶颈,“在我这个龄和职位,继续待在外企的话后面的路已经很清楚,升职上遭遇玻璃天花板,龄上经不起高强度的工作”。
另一方面,不少人由于产业大环境的变化,“金饭碗”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
科锐国际早期的客户源100%都是外资企业;公司成立五六时,2000左右,科锐国际开始与包括华为、李宁[5.90 -3.44%]等在内的本土企业有初步接触;到2004、时,公司明确将发展内资企业客户作为重点,彼时内资企业所占科锐国际客户源的比例还很低;从、以后,内资企业的业务能占到科锐国际总业务的百分之二三十。“在高科技、互联网这些行业,外资客户与内资客户的比重甚至是四六开。”
刘峰认识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经理,在90代末或者2000左右,他们的职业很让人艳羡,而现在职业的“含金量”已经大不如以前。“那时候的外企中高层,买两套房子很正常,但是你今天进到外企,即使给你八千、一万块钱月薪,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房子呢?同样是薪水,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职场危机提前而至,在发达国家,焦虑、无措、迷茫等中职场危机的表现通常发生在45~55岁,但是在中国却提前了近10。
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x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
退休或重返职场?
参数未知的将来
“退休”,对当下这个人群来说,几乎是一种奢望。
李强是一家私企的老板,早做生意赚了几百万后觉得足够将来生活了,便结束了生意,开始安享生活。可是不到十,他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预设的轨道。“十前几百万足够一个人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几房价、物价会涨成这样,现在几百万还算个啥。”“安享”计划泡汤的李强不得不重整旗鼓,再次创业。
刘峰身边也有朋友有过和李强类似“提前退休”的经历。这位朋友为了移民加拿大,在事业发展最顺风顺水的时候,提前结束在中国国内的工作,在加拿大当地随便找了个工作。待到移民必须的居住时间期满后,这位朋友想再回中国来发展,却发现已经错失了事业发展的最好机会。
对于至少还有些“家底儿”的李强等人来说未来虽然艰难,但还不至于毫无保障,对于更多的中职场工作者而言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这一群体的焦虑。到底有多少资产未来才可以安枕无忧?没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20多前,大学每的学费只有200元,现在有些专业已经冲上万元,增长了约50倍。中国青报社会调查中心曾有一项7625人参与的调查统计称,尽管78.8%的人认为和十前相比收入增加了,但是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前更重了。有人估算了近四十来中国人结婚的成本:70代末是600元,80代是3000元,90代是3.3万,21世纪达56.6万,越来越贵的中国式婚姻。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但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却远没有跑过物价上涨的速度。
“在过去几十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中层人群,其实没有好的政策来扶植他们。”刘峰感慨,中层的赋税很高,高到很吓人的程度,而另一方面,国家给予这一阶层的福利几乎是零。“比如说我每月交那么多钱的税,突然有一天失业了,却发现我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对于这一现状,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认为,日本企业的员工对于未来的焦虑感要比中国低得多,“日本有约定俗成的终身雇佣制以及与其相配合的功序列制、企业工会。这是日本的三大神器。”白益民介绍,在日本的企业中,企业不会轻易裁员,功序列制是指工资待遇按员工的资历慢慢增长,所以一旦进入一个企业,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在这家公司大概享有的工资待遇水准。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是否应该采用终身雇佣制的争论一直存在,白益民的看法是一些特定的企业可以尝试这种制度,这对于企业人才的积累、技术的传承以及员工对生活的安全感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异化的人性
“被高速”的一代
曾小亮认为,整个社会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同时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因为人不可能变成一个经济动物,人有内在的自尊、自我,有对幸福感的追逐,经济并不能满足人们更深的快乐。“很多人在有了基本的物质保证之后,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寻找新的幸福之道。”
“你会发现人们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有一脉相承的地方,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曾小亮注意到,中阶层的这种集体性焦虑和迷茫,曾经出现在美国的上世纪七八十代,中国台湾的九十代。
在中国,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让管理人才的职业晋升速度超过了心智成熟度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过分注重分数,而忽视了心灵的成长,此外对经济发展的过度追求,也让这一群体缺乏对生活的整体观。
“升迁官能症”在中层人群中就相当普遍。“或是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是能力不够、提拔太快,被提拔上去以后,会发现很多事情自己没有能力驾驭了。”曾小亮认为,因为心智的成熟速度赶不上社会角色的提升速度,很多中层人群在职场角色擢升后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跟同事的关系、家庭的问题,突然就会觉得自己扛不住了。我曾经在专栏中提到过,在这个状态下要学会用一些方法去调试,这就涉及到很多大的课题了。我觉得这跟人才的储备也有关系,经济发展太快,人才储备不够。”
这种对周遭事物掌控能力的欠缺也极大地加剧了这一人群的焦虑感。
一直以来,中国都推崇GDP增长的神话,认为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水平,解除贫困状态,增强综合国力。在这种背景下,“GDP崇拜”成为一种普遍情结,唯效率主义或独尊经济指数的发展成为主要甚至惟一的取向。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也导致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国民教育、就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人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领域的发展就被不同程度的牺牲掉了,当置身经济发展大潮的主流阶层人士行至中才发现自己忽略了身体,忽视了家庭,却并没有从过快发展的经济中获得多少幸福感,甚至于找不到自己的未来。
近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美国联邦政府和英国内阁甚至拨巨资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等专家坐镇,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幸福经济”越来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曾有人发问,如果GDP的增长不能让人们更幸福,政府为什么还要致力于GDP的增长呢?当下“茫一代”既是推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蚂蚁雄兵,也是被经济高速发展“副作用”所中伤的一代,他们是否幸福、如何才能幸福,是中国社会经济代际变迁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