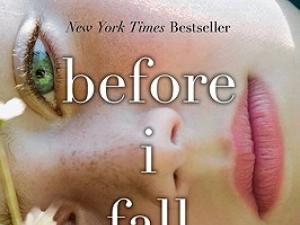电影武训传视频观后感【优秀篇】
更新:2017-06-01 13:52:30 来源:思而学教育网 www.gxscse.com
武训先生是一个蒙尘的明珠,兴义学褒贬不一,曾一波三折,最终对他的兴学精神多持肯定、景仰、效法、弘扬,他那种"为众谋"精神扎根于人民心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电影《武训传》视频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电影《武训传》视频观后感【篇一】
武训先生(1838—1896),行七,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原无名,名“训”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
武训自21岁(清咸丰年间)起,武训以行乞的方式集资兴办义学,目标是“使他们(贫苦人家子弟)无钱也能读书,使他们读了书不再被人欺”。
在30多年的时间内,武训乞讨的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省。武训在行乞过程中,为自己设计了一个奇特的造型以吸引人们的目光:先是卖掉右边的辫子,剃光了右边的头发;后来又剃光了左边的头发,而在右边又留起一撮头发。也表演“拿大项”、“蝎子爬”的节目,或给人当马骑,供人取乐,甚至吃粪便、砖瓦,以得到办学的款项。

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已经靠乞讨所得的款项置买了230亩田地作为学田,积蓄3800余吊钱。于是他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兴办起第一所义学——崇贤义塾。学校建成后,他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就招收了50多名学生,学费全免,办学所需经费就从他置办的学田中支出。在这之后,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
1890年,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22年(1896年),临终那年,在临清建成了御史巷义塾(现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为了一心一意兴办义学,甚至坚持一生不娶妻室。
武训一生劳苦,对自己又十分节俭,终因积劳成疾,于光绪22年(1896年)4月23日,在临清御史巷义塾内(现临清武训实验小学)含笑去世,终年59岁,葬于堂邑崇贤义塾东侧。有万人以上群众,包括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全体官绅,参加了武训的葬礼。
武训的义举在当时受到各界普遍高度的评价,山东巡抚张曜下令免征学田钱粮和徭役,并捐银200两。光绪皇帝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又敕建“乐善好施”牌坊。
武训是清朝末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个乞丐,靠着乞讨敛钱,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起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余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之多,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所以有人称颂他是“千古奇丐”(冯玉祥语)。
电影《武训传》视频观后感【篇二】
今天终于没有错过人生中的重要时刻,在影院小厅看了胶片版的有些许残缺的电影《武训传》。以现在的观影习惯来看,电影语言本身显得有些落伍了,慢条斯理的叙事,充分浪漫的情感宣泄,还有那些明显的表意符号贯穿于整部电影。
毕竟已经五六十年了,当年感染观众的方式有点显得可笑,不大适合今天快节奏的欣赏习惯。至于影片的思想内容,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近乎三十年的积淀已经让《武训传》本身从艺术到政治有了一个近乎尸体解剖似的分析和介绍,动用了从天文望远镜到高倍显微镜的各种工具,各个层面,各个角度都有所涵盖。所以笔下无言也有情可原,于是只是回到宿舍,翻看了能见的一些当年文字,囫囵吞枣的浏览了一遍。
所看书目不过《中国电影研究资料》吴迪主编、《中国电影理论文选》罗艺军主编、《中国电影百年》李多钰主编三本书而已,权当了解大概,故而不敢妄称研究,不过有些许断想而已。
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和平反
《武训传》的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发端(《中国电影百年》语)。早先国内放映的时候,可以算是好评如潮的。事实上,正是因为“好评如潮”,才更为突显其显现出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上海的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的媒体上还有关于编导孙瑜和演员赵丹对于影片的经验介绍性的文章,可见当时有树立典型的苗头:名导和明星的珠联璧合。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应该重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随后而来,掀起了批判风潮,从电影摄制人员扩到到整个文艺界,从具体的“武训评价”到抽象的阶级立场,终于成为政治性的运动。此后《武训传》永远都不享有纯粹的文艺评价,而紧紧的和政治发生了关系。1985年胡乔木的一段简要讲话,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对《武训传》的平反,还是以政治运动的清算方式开始的。
孙瑜当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编导〈武训传〉记》,只是半回忆录性质的,创作上的探讨较少,《编导〈武训传〉前后》则倾向创作经验的内容多一点。而赵丹的《我怎样演武训》的理论研讨价值也很大。相信当年的一些正面评论,也是较为集中在艺术范畴内的讨论和批评。这可以在后来批判风潮中的一些文字中找到依据,比如李长之先生1951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文章《我在关于〈武训传〉的讨论中得到了教育》写道:
“我过多地评论了《武训传》电影和《武训画传》的艺术,太轻太淡地而且是(不正确地)触及了政治意义。这不免是单纯技术观点,这不免是西方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的形式主义的美学的影响。因为缺乏对政治意义的足够的重视,所以就是艺术标准的批评论,也就犯了错误。”
此段文字或可印证。
5月的社论一经抛出,形势急转直下。批评夹杂、混淆甚至歪曲了政治因素和政治立场,用文艺批评的手段搞政治,用政治的方式搞批评。于是雪片般的评论飞满全国,采取艺术分析和政治品评“嫁接”的方式,炮制出炉了一篇又一篇的批判和检讨稿件。仍以李长之先生的同题文章为例,在前引文字之后,紧接便着例证了他的“错误”:
“例如我指出,武训电影之‘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并没有提高它的艺术性,反之,是降低了它’,然而理由呢,是:‘损害了武训事业的严肃性’。其实,武训事业根本没有什么价值,也就说不上损害不损害它的严肃性了。可见不把政治放在第一位,艺术性的批评是不会正确的。”
如果说关于“热闹和罗曼谛克底抒情”算是艺术层面的分析,那么对于“武训事业”的评价实在是无由的牵强。然而各地这类稿件之多,是无法想象的。江青更是亲自带队实地考察,不但洋洋洒洒的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还树立起了“宋景诗”这一光辉的反抗的正面的形象来和武训形成对比。总之,最先的政治定论为《武训传》的政治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了永久的记号。是这之后关于《武训传》的评价都离不开了政治。
至于后来的平反,仍然是政治化的。1983年万里,1985年胡乔木分别都表示对于《武训传》的评价有失公允,而此时已经处在对“文革”拨乱反正的政治工作中了。对于《武训传》的平反,也自然划归到了政治清算的一部分。事实上,在其后的多数关于《武训传》的评论文章中,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录,还是研究者的学术文章,都已经舍弃了电影艺术的标尺,而成为研究“谁之过?”的历史淘金。比较典型的就是将《武训传》批判归结为江青个人阴谋报复行为,是对知根知底的赵丹等前同事的个人迫害。
电影之后尽管经常有人提起,在影史上留有一笔,却鲜有关于艺术成就的评价和概括。《武训传》成为了政治或者文化的一个符号。
批判《武训传》的武器
江青借着批判《武训传》的风潮,组团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该文考据丰富,旁征博引,实在是集大成的典范之作。可见当时的人们确实有股韧劲。我和大学同窗还曾就此事感慨过。从《武训传》公映到《调查记》成文发表,不到三个月。“调查取证”,编撰行文,还能在浩瀚史海之中找到“宋景诗”这号人物,专门用于对于武训的回击。这种独特视角和博学,现在依然销声匿迹了。
如今荧屏银幕上充斥着各种耳熟能详的情节和段子,都是同样的桥段不过换个时空,换个身分,就能堂而皇之走进大众娱乐的视野。不是各种篡改传说,就是“秘史”系列。蹦蹦跳跳的表现着后现代的不屑和疯癫,骂骂咧咧地糟蹋消费者的智商和品性。没有丝毫智慧的胡闹在媒体上,相比之于当年江青的目标和手段,简直是不值一提。
如果说《武训传》是个政治和文化的符号,那么这个符号最起码指代的是一种“严谨持重无所不用其极的改造”。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能根据武训的人物和形象的反面,迅速寻找并打造相应人物和形象予以回击。这种创造力不仅仅是模仿,更是水平。迪斯尼素来以改造他国童话传说闻名于世,对中国《花木兰》的改造,换来的只是上海动画电影制片厂挖掘原著的《宝莲灯》,而同是讲述母子亲情题材的动画片,迪斯尼随之而来的《人猿泰山》把亲情提高到了一个人兽间的争议高度。对于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迪斯尼采取精彩讲述的方式,梦工厂则选择了完全解构。《调查记》及“宋景诗”完全证明了这样的创造力并非国人所缺,只是渐渐的淡忘了。或者说,没有缺失也没有淡忘,只是从来没有用在创作或者娱乐这些形而上的无用方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实践到“为人处事”的能力上了。
尽管并非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至少证明着,一段时间内,国人国片的创作是有激情且有活力的。这让今天的所谓“繁荣”汗颜不已。
《武训传》及历史的武训化
夏衍先生在《武训传》拍摄过程中就曾提出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说法,这大概是从艺术角度的评价。而纵观《武训传》的全片和历史,让笔者不禁有了不同的理解和结论。
《武训传》中的武训形象,是悲剧性的。几次三番的看着并经历了穷人吃“不识字”的亏,于是立志兴建义学,为穷人家的孩子无偿的提供教育环境和教育机会。然而,当小孩读书给武训解释“学而优则仕”的圣贤道理时,武训对自己的做法深刻的质疑了。事实上,这一点也是最早关于武训批判比较集中的部分,即武训的义学虽然是济世的,但终归还是向封建传统和封建制度的妥协。编导们当然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这一点认定这个形象的深刻悲剧性:妄图利用敌人的游戏规则消灭敌人,而实际上却是为敌人培养了更多的有生力量。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一特性。
武训由于目不识丁,不懂得礼数,没见过世面,自然对于儒界官场的规则一窍不通。被泼皮无赖的欺骗不过是皮肉之苦,被官僚政客的利用才是更为尴尬和令人焦虑的。武训的义名远播,惹得各级官僚都用足了心思在他身上下文章,下到一县之长,上到太后皇上,无一不以他为工具,标榜政绩,粉饰太平,收揽人心。而武训对此则毫无察觉。这是武训被利用的第二特性。
回过头来看《武训传》批判的历史,那些批判、反批判的文章,哪一篇不是对“游戏规则”的无奈适应?“艺术分析加政治品评”模式不正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妥协和及这种妥协的认定?而那些批判和反批判的人们,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对于政治的依附,最终成为政治工具的悲剧命运。当年或出于无可奈何,或出于随波逐澜的批判,不过是政治风潮中的一朵浪花。动用想象力写出文章发表的和发挥创造力挖掘历史造型的,都是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已。至于平反时分,站出来高声怒骂的,低下头深刻反思的,也说不清是真情流露还是随声附和。
《武训传》里的反派张举人,自以为手执笔端,“一字令人生,一字令人死”,似乎笔杆子的力量大于刀把子。其实还是没看见自己的脑壳子,早已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了。那些利用武训之名,或揽人心,获得好处的人,自己已然“武训化”了。他们不过是在别人的身上实践着从自己经历中学到的宝贵经验而已。
总而言之,无形的制度不但规定了所有的人都在体制框架内游戏,而且规定着胜利者的属性和位置。所有游戏中的人们不具备相应的属性和位置,就永远是胜利者玩物。
而所有人都是游戏规则的玩物。
美国悬疑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集锦】
《忽然七日》一个超现实的故事,讲述了死亡与重生、觉醒与救赎的主题,发人深省。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忽然七日》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美国悬疑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篇一】 人,没经历过某些,永远不会懂得某些,这是人性基础设定。虽然大量文字影像言教身传试图告诉未开化的人性很多道理,但是很可惜,且不提洗脑的扭曲和智力悟性基因的限制,无用功且误判误导,不如不用拿出来糟蹋。剧本台词演员……看得我很尴尬,群演不错,我确实老了,看到有人看哭了,我表示羡慕你的年青。努力跳着看到结局,想知道怎么自圆其说而..…[详情]
忽然七日电影观后感优秀【多篇】
《忽然七日》来自今年一月份圣丹斯电影节的首映单元的剧情电影改编自萝伦奥立佛的同名畅销小说。下面是相关的范文,快来围观吧。 忽然七日电影观后感【篇一】 《忽然七日》是由Zoey Deutch主演的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作者是劳伦·奥利弗。主要讲述了一个死亡与重生、觉醒与救赎的故事。萝伦奥立佛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莎曼珊金斯顿(柔伊德区 饰演)在2月12日晚上发生意外,她感觉自己将永无止尽地坠落,但一个声响打断沉默,她醒过来了,闹钟已经响了二十分钟。现在是早上六点五十分,2月12日。意外过后,莎曼珊发现自..…[详情]
悬疑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精选【二侧】
生命和脆弱,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明天。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没做,有很多人我们都还不懂得珍惜,有很多话我们还没有讲。 悬疑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篇一】 也许,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都曾想过“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是否具有某种意义?”我也很多次想过这个问题,在清冷的早餐,在昏昏欲睡的午后,在沉闷的傍晚,在寂寥无边的深夜,独自窝在椅子上,关着灯,思绪像铺天盖地的黑纱将我笼罩在其中。视线凝固在空气中,呼吸像时光中流淌的溪流,那是一种悲伤感觉,一种空洞失落的悲..…[详情]
美国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精华篇】
《忽然七日》是由小说改编的电影。yuwenm小编整理了美国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欢迎欣赏与借鉴。 美国电影《忽然七日》观后感【篇一】 15年读了这个小说,第一感受是,这故事真适合拍成电影。 等到今年终于有时间,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了,才发现人已经拍成电影了...... 这真是一部忠于原著的电影。 读小说时的画面被一一还原在了银幕上。出身在纽约的女导演Ry Russo Young对这个故事一定也有自己真实的体验。从头到尾没有什么多余的镜头,有几个画面唯美得让我想到了暮光之城,换成我一定拍不了她这么美..…[详情]
公益电影《20:16》观后感【汇总】
《20:16》经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电影。小编整理了公益电影《20:16》观后感,欢迎欣赏与借鉴。 公益电影《20:16》观后感【篇一】 励志影戏《20:16》已于5月18日正式在全国上映,已经七年没有在大荧幕上呈现的香港著名演员刘松仁担纲这部影戏的男主角,让浩瀚粉丝惊喜不已。 影戏《20:16》是按照香港叶氏化工团体主席叶志成的真实创业经验改编,任意发B2B,报告了他与妹妹叶子涓在上世纪七十年月从零格斗数十年,到乐成成立“化工王国”的艰苦创业过程。据悉,影戏的导演编剧历时八年创作了这部影片,旨在但愿年青人能从影戏主人..…[详情]
2017年励志电影《20:16》观后感
电影《20:16》是根据香港叶氏化工集团主席叶志成的真实创业经历改编。以下是小编整理的2017励志电影《20:16》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2017励志电影《20:16》观后感【篇一】 电影《20:16》以叶志成的创业历程为创作蓝本,讲述上世纪70年代,一批国内青年跋山涉水跨海游泳来到香港,他们从零打拼为社会做出贡献。电影的主人翁便是其中一员,他们兄妹二人于1971年以港币4,000元为资金,在香港一个占地40平方尺的铁皮横门艰苦创业,几经波折后事业终有所成。电影由中迈有限公司、上海华大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香港著名男演员..…[详情]
刘松仁主演电影20:16观后感【优秀】
《20:16》观后感电影传达出的坚持梦想、用心拼搏的正能量,并见证了紫荆花涂料集团的艰辛创业历程。下面是刘松仁主演电影《20:16》观后感,快来围观吧。 刘松仁主演电影《20:16》观后感【篇一】 电影《20:16》以一位成功企业家与怀揣梦想的女记者之间的励志情谊为主线,重现了叶志成及妹妹叶子涓艰苦而传奇的创业历程。这部电影以70年代的广东省乒乓球运动员选拔赛入手,时年16岁的叶海鹏以20:16领先对手,有望成为职业运动员改变家族命运,随后却频频失误而遗憾落败。不甘平庸的叶海鹏带着妹妹叶子涓历经八小时夜游,赤脚走过数..…[详情]
加勒比海盗5观后感精选【多篇】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嬉戏的幽默感总会带来无穷的乐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加勒比海盗5》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详情]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之死无对证观后感【集锦】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5终于出现了,那么关于其观后感怎样,下面是相关观后感的范文,快来围观吧。…[详情]
2017年荡寇风云电影观后感三篇
《荡寇风云》故事发生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戚继光率领3000戚家军在台州附近的花街、新河等地与20000入侵倭寇周旋,九战九捷,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史称“台州大捷”。此战之后,倭寇不敢进犯浙江,浙江倭患基本荡平。…[详情]
历史战争影片荡寇风云观后感【精华篇】
《荡寇风云》凭借120多分钟的片长,尽可能用多个桥段丰富戚继光这个人物,导演跑遍了戚继光的所有战场,参观了多个历史博物馆,同时亲赴日本松浦的王植旧址,目的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用电影语言真实还原那段过去,在观影过程中可能会觉得冗长,却一点不觉得乏味。下面是《荡寇风云》观后感,快来围观吧。 历史战争影片《荡寇风云》观后感【篇一】 王朝正规军依仗人数优势获胜的剿匪战争,应该没有什么可看。戚继光抗倭的传奇性在于,戚家军人数较少,而且是从乡民中培养的类似于特种部队的军人。其对手倭寇的成分复杂而且战斗力惊..…[详情]
夏天19岁的肖像电影观后感【多篇】
悬疑是《夏天19岁的肖像》的一大王牌。这不仅得益于剧情对悬疑点的智巧埋设和有机勾连,也离不开演员对角色的渗透研析和合理塑造。下面是相关的观后感,快来围观吧。…[详情]
悬疑爱情青春电影夏天19岁的肖像观后感
《夏天19岁的肖像》影片改编自日本“本格推理大神”岛田庄司的同名原著,兼具爱情和悬疑的双重魅力。男主角黄子韬此前的路演热度爆棚,随后开启的数场超前点映口碑获赞。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夏天19岁的肖像》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 悬疑爱情青春电影《夏天19岁的肖像》观后感【篇一】 全片讲述了一个大学生偷窥爱上扬州瘦马小姐姐并被其包养,在小姐姐完成每个男生都要经历的性启蒙女神使命后功成身退的故事,中间夹杂炮灰和炮灰的备胎。 影片从黄子韬炫酷骑着机车装着13结果摔断腿开始,尽管我不懂为何豪宅会建在医院对面..…[详情]
黄子韬夏天19岁的肖像观后感【集锦】
电影《夏天19岁的肖像》除了令人备受期待的青春元素,在原著的基础上改编加入的悬疑线更突破了以往青春片的类型。下面是相关的观后感,快来围观吧。…[详情]
傲娇与偏见电影观后感【汇总】
《傲娇与偏见》和《傲慢与偏见》仅一字之差,不细看或许还会认错。“傲娇”又是当下流行词汇,有点欲擒故纵,有点萌。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傲娇与偏见电影观后感,希望对你有帮助。…[详情]
爱情电影傲娇与偏见观后感三篇
不少人在观《傲娇与偏见》后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盛赞影片魔性十足全程爆笑。小编整理了《傲娇与偏见》观后感,欢迎欣赏与借鉴。 爱情电影《傲娇与偏见》观后感【篇一】 有笑点有泪点的电影,三个主演全程演技颜值在线,还是值得一看的。只是高伟光的戏份少了点,看得有些不过瘾。 文艺色彩还是浓厚了一些,女主的故事过于苦情,有点假。男主又是普通的高富帅套路。而且两男争一女,加上一个渣男前男友,感觉有点满满的套路。 不过还有有一点不一样的小惊喜。比如男主愿意放弃事业陪女主的理由(其实也不太意外)。比如女主..…[详情]
南粤党旗红观后感心得体会精选二侧
《南粤党旗红》观后心得体会1:为迎接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营造团结鼓劲、弘扬正气的浓厚氛围,×××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观看了《南粤党旗红》专题片,观后并开展座谈交交流。交流中,党员们纷纷各抒己见。其中×××、×××等两位同志发表了自己深刻的观后感;党支部书记×××同志最后向全体党员提出了要求:广大党员要撰写观后感和学习体会,要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党支部高度重视此次收看学习的专题片,并采取集中观看和个人学习相结合的形式,还强调要求,..…[详情]
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观后感心得体会【精华篇】
导语:通过电影《库尔班大叔上北京》的重映传递真挚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温库尔班·吐鲁木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下面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的库尔班大叔上北京心得体会,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一:库尔班大叔上北京心得体会】 组织大家观看了电影《大河》及《库尔班大叔上北京》,2部影片都非常感人。特别是《库尔班大叔上北京》这部片子对我的触动很深。 片中记录了库尔班被地主巴依迫害有家不能回,在胡杨木树丛里生活,与现实生活脱离,最终被解放军解救出来。在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分得了土地房产,找到了失散多年..…[详情]
2017年专题片南粤党旗红观后感
《南粤党旗红》专题片主题是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全面推进从严治党。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南粤党旗红观后感,欢迎阅读。 【1】专题片南粤党旗红观后感…[详情]
关于南粤党旗红观后感心得体会
南粤党旗红专题片给党员们带来了心灵上的触动、思想上的洗礼和行动上的鞭策。下面是思而学教育网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南粤党旗红观后感心得体会,欢迎阅读。 【1】南粤党旗红观后感心得体会…[详情]